界面新聞記者 | 劉婷
美日貿易協定日前塵埃落定,日本商品進入美國將面臨15%的“對等關稅”,相比月初時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的要價低了10個百分點。這筆交易再次體現了特朗普在關稅戰中“雷聲大、雨點小”(Trump Always Chickens Out,Taco)的行為特征。
分析師指出,關稅對美國金融市場和經濟的負面沖擊是決定特朗普立場搖擺的主要因素,此外,司法挑戰、全球供應鏈深度綁定、以及來自貿易伙伴的反制等現實因素也會掣肘其高關稅計劃落地。
7月初以來,特朗普已對20多個國家/地區發送了“征稅函”,通知其最新互惠稅率,即所謂的“對等關稅”。至今,美國已與印度尼西亞、菲律賓、日本達成了協議,和“征稅函”提到的稅率相比,三國最終面臨的“對等關稅”分別下降了13、1、10個百分點。

以日本為例,當地時間周二晚間,特朗普宣布對日本征收15%的對等關稅,較此前威脅的25%下調10個百分點。作為交換,日本承諾向美國投資5500億美元,并降低汽車、大米等農產品的進口貿易壁壘。日本首相石破茂周三確認了這一協議。?

此外,7月2日,美國宣布與越南達成協議,產自越南的商品進入美國將面臨20%的關稅,這一水平和4月2日相比下降了26個百分點。更早之前,在和英國達成的協議中,美方雖然保留了10%的基準對等關稅,但是下調了部分行業的進口關稅,比如汽車關稅由27.5%降至10%,鋼鐵和鋁關稅從25%降至0,作為回報,英國同意進口美國食品和農產品。
由于特朗普多次在關稅問題上搖擺,因而被西方媒體嘲笑為Taco。這個詞是今年5月由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者羅伯特·阿姆斯特朗(Robert Armstrong)創造的,阿姆斯特朗指出,特朗普的政策邏輯是先發出最要命、最寬泛的關稅威脅,然后不斷退縮,收回、暫停和提供各種例外的條款。
以“對等關稅”為例,特朗普在4月2日宣布向貿易伙伴開征后,引發美國金融市場暴跌,迫于各方壓力,他在4月9日宣布暫緩對部分貿易對象征收高額“對等關稅”90天,但維持10%的“基準對等關稅”;7月9日本是90天暫緩期的截止日,他又下令將暫緩期延至8月1日。
對于特朗普在關稅問題上“雷聲大、雨點小”的行為模式,分析人士認為主要有四個原因。
首先是來自金融市場的壓力,一旦投資者擔心關稅會對美國經濟造成重大負面影響,進而導致市場動蕩,特朗普就會迅速妥協。
對外經貿大學國際經貿學院教授崔凡對界面新聞表示,特朗普是否退縮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美國經濟的表現,比如,4月份的退縮行為正是由于激進關稅直接影響到美國經濟預期。
凱投宏觀首席亞太分析師Marcel Thieliant對界面新聞表示,他們一直堅持認為,特朗普最終會放棄最初威脅的高關稅。“他往往以‘最高要價’開場,但往往在市場和經濟現實面前碰壁。”Thieliant說,因此大多數國家最終將僅面臨10%左右的“對等關稅”。
4月2日,特朗普高調宣布對近60個國家和地區征收10%-50%不等的“對等關稅”,幅度和波及范圍遠超預期。經濟學家表示,在不考慮其他國家反制的情況下,“對等關稅”將使美國進口減少30%左右,在供給短缺的情況下將大幅推升通脹水平,進而拖累經濟增長,美國經濟有可能陷入滯脹境地。受此悲觀情緒推動,4月3日至4日,僅僅兩天之內,美股就蒸發超6萬億美元。一周之內,蘋果、微軟、亞馬遜、特斯拉、Meta、英偉達、谷歌等美股“七巨頭”的市值累計損失1.8萬億美元。
截至目前,特朗普關稅還未對物價造成顯著影響,分析人士指出,這主要是庫存緩沖效應所致。一方面,去年四季度以來美國商品庫存持續下降,引發補庫需求激增,另一方面,在高額“對等關稅”被暫停的情況下,各國外貿企業持續“搶進口”,亦對美國庫存形成較大支撐。
美國勞工統計局上周公布的數據顯示,6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同比上漲2.7%,漲幅比5月擴大0.3個百分點,環比上漲0.3%,漲幅比上月擴大0.2個百分點。盡管通脹有所上升,但并未顯著超出預期,數據發布后,投資者對美聯儲在7月和9月降息的預期進一步下降。
不過,多數分析師認為,關稅對美國通脹的影響將從下半年開始顯現。
保德信固定收益首席美國經濟學家Tom Porcelli對界面新聞表示,實際關稅稅率每上升1%,將推高美國物價約0.06個百分點。他指出,進口貨品占美國核心個人消費支出約10%,而近期一項賣方投資者調查顯示,約60%的關稅成本將被轉移給消費者。
浦銀國際首席宏觀分析師金曉雯在研報中表示,預計關稅對美國通脹的影響在7-8月的CPI數據中會有更明顯的體現,核心商品CPI或繼續上行,成為左右核心CPI走勢的關鍵因素。
她還表示,在美國的關鍵貿易伙伴中,目前僅有日本和美國達成協議,而加拿大、墨西哥、歐盟和中國仍在談判中,這四個地區2024年在美國進口的占比合計超過六成。若對這些國家(地區)征收高額關稅,其影響不可小覷,或顯著影響美國經濟增長和通脹率。
其二,特朗普的“交易的藝術”引起貿易伙伴的反感。
浙商證券分析師廖靜池等分析師指出,Taco源于特朗普“求其上者得其中”的博弈策略。他以最終達成談判為目標,或傾向于先進行“壓力測試”,再退一步以雙方都能接受的條件和談。但是其本身追求的多重目標之間存在內在矛盾性,加上中國等貿易伙伴在談判中的話語權提升,均使得特朗普的“極限施壓”難以為繼。
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副所長徐奇淵在日前發表的一篇文章中稱,即便是美國的盟友國家,對特朗普關稅策略的反感和抵觸情緒也在悄然積累。“特朗普多次反復的Taco行為,也讓市場投資者和各國政府對‘交易的藝術’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他說。
其三是來自供應鏈的制約。分析人士指出,在當前全球供應鏈深度整合的背景下,高關稅將導致美國本土制造業成本激增,這在美國政府大力促進制造業回流的背景下尤為重要。?
天風證券分析師譚逸鳴在研報中表示,從美國與英國、越南和印度尼西亞達成的初步協議來看,這些協議有兩個共同特征,一是特朗普對供應鏈安全的重視,二是迫使貿易伙伴購買美國商品。
例如,在美英協議中,英方承諾努力滿足美國對輸美鋼鋁產品供應鏈安全以及相關生產設施所有權性質的要求。在和亞洲伙伴的協議中,美方要求越南購買20億美元農產品,印尼購買150億美元的能源產品、45億美元的農產品和50架波音飛機;日本則必須降低汽車、大米等農產品的進口壁壘,同時,日方表示將通過半導體、鋼鐵等領域投資強化美日供應鏈合作。
“在全球供應鏈深度整合的背景下,高關稅只會催生轉口貿易等規避手段。這場看似兇猛的政策風暴,最終效果或如2018年關稅政策般‘雷聲大、雨點小’。”華泰期貨研究員陳思捷指出,回看特朗普第一任期,其任內多數的關稅措施最終通過豁免變相軟化。
此外,美國國內司法挑戰也是影響“對等關稅”的重要因素之一。
5月28日,美國國際貿易法院裁定特朗普4月2日基于《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對多國征收對等關稅“越權”,禁止其生效。不過,經特朗普政府上訴后,美國聯邦巡回上訴法院暫停了前述禁令,定于7月31日開庭審理。
摩根大通認為,若特朗普政府被裁定敗訴,不僅可能使8月1日的貿易談判截止日期和已達成的協議變得“毫無意義”,還可能導致特朗普政府尋求其他法律工具,從而開啟一場長達數月、更加難以預測的貿易動蕩期。“這場司法對決或從根本上改變當前的貿易對峙局面,其影響甚至可能超過了8月1日的談判大限。”摩根大通警告稱。
徐奇淵認為,最有可能的結果是,最高法院部分支持特朗普政府的關稅政策,比如選擇性支持部分關稅措施,或者在事實上延長暫緩執行禁令的時間,為特朗普推進替代關稅的全面生效贏得時間。對于法律程序可能帶來的不確定性,特朗普團隊也早有準備,已經完成和正在進行中的232、301條款調查,將為其提供替代性關稅工具。
232條款指的是《1962年貿易擴展法》的232條,它授權美國總統以“國家安全”為由限制進口,主要針對特定行業。比如,今年以來特朗普多次援引該條款對鋼、鋁、銅等產品征收高額的進口關稅。
301條款指的是《1974年貿易法》的301條,允許美國在認定他國存在“不公平貿易做法”時,對該國商品加征報復性關稅,針對特定國家。特朗普在其第一任期就利用301條款對中國商品征收懲罰性關稅。
美國政府數據顯示,自4月實施“對等關稅”以來,關稅收入迅速上升,僅6月就達到266億美元,是平常水平的4倍,今年上半年關稅收入飆升至872億美元。據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分析,截至6月底,10%的基準對等關稅已帶來超過177億美元收入,針對汽車行業的特定關稅也貢獻了超過107億美元。
Porcelli表示,根據美國關稅收入的增長,估計6月份的實際關稅稅率已略高于10%,預計實際稅率最終將落在15%至20%之間。
摩根大通認為,在5月12日中美日內瓦經貿協議達成后,美國實際有效關稅稅率達到13.4%。考慮到232條款,未來稅率最高或至17.5%,這一水平雖然遠高于2024年的2.3%,但低于4月2日“對等關稅1.0版”時的23.1%。中金公司預計,8月1日后,美國有效關稅稅率大概率落在15-16%,最高或至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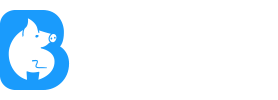








發表評論